每到6月,随着雨季的来临,昆明的木水花野生菌市场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到了7、8月份,市场里的狂欢气氛达到高潮。松茸、牛肝菌、块菌、松露、羊肚菌,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。新鲜的泥土混合着菌子独有的醉人气息,菌子的季节来了。
早先,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。5月,或者6月,第一种蘑菇开始在草坡上出现。就是那种可以放牧牛羊的平缓草坡……一场夜雨下来,无论直立的茎或匍匐的茎都吱吱咕咕地生长。
在阿来的《蘑菇圈》一书中,人们将蘑菇视为来自造物者的神奇,象征着整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界。巨大而复杂的生命网络中,树林的落叶枯木下,都成为无数菌类的乐园。人们采食菌类,菌类再将养分回收土壤,森林于是开始有了意义。
中国的历代本草中都不乏各种菌类的书写,作为一种食材,它是餐桌上的风雅颂,是厨房里的家春秋,记录着民族的交流与历史的变迁。
《吕氏春秋》里记载味之美者,越骆之菌;杨万里曾在《蕈子》一诗中写下响如鹅掌味如蜜,滑似莼丝无点涩,念念不忘菌子的芬芳与鲜滑。在古代,人们为了区分不同的菌类,称之为䓴以表柔软轻薄,称之为蕈意味着生于树林,称之为菌则散布在田野,还有专门描述香味独特的芝。
就像《蘑菇圈》中描述的那般,蘑菇或是菇渐渐成为人们对大型菌类的总称,是在宋代之后的事了。南宋末年,蒙古大军入主中原,而后建立元朝,也带来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。蒙古人习惯将食用菌叫作 moog,渐渐在民族融合中的语言交织中,这个发音渐渐被取代为菇,并被在前面冠以蘑字,由此打败了䓴蕈菌芝,渐渐成为中原人对所有食用菌的称呼。
明清时期,越来越多的食用菌流向了中国人的餐桌,清朝的《闲情偶记》与《随园食单》中都出现了大量关于烹制蘑菇的做法。直到今天,除了在菌类资源极为丰富的云南,人们用蘑菇指养殖菌、菌子指野生菌,绝大多数地区依旧习惯于东北的榛蘑、华北的平菇、江浙的香菇……以蘑菇二字代之。
而狭义上的蘑菇,便是市场和超市最常见的白色口蘑,西方也有对应的叫法普通蘑菇(Common Mushroom),指的便是菌属的双孢蘑菇 (Agaricusbisporus)。这一种类的蘑菇肉质肥厚,也是西方最常见的食用菇之一,像是白色口蘑(Button Mushroom)、棕色口蘑(Chestnut Mushroom)及波特菇(Portobello Mushroom)都属于这一范畴。
与之对应的野生菌(Wild Mushroom), 可以看作是西方常见野生蘑菇的合集,通常打包售卖,随时令和季节而变化,一般不做细分。比较特别的是意大利人,将蘑菇融于各式米面主食的他们,给蘑菇起名时总会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像是金黄色的鸡油菌(Finferlo)是可以吃的小锅子,肥厚多肉的牛肝菌(Porcino)则是小猪的昵称。
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边界决定世界的外延,人们对菌类的认知,也在无数对它的称呼与记载中渐渐丰满。
人类食用真菌的历史悠久,无论在东方或西方,人类认识菌类,学习食用菌类,与菌类共生的历史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。无论是亚马逊热带雨林,还是东北大兴安岭的密林;无论是加州大瑟尔海湾的山间,还是被朝露打湿的蒙古草原,菌丝都在黑暗中破土生长。在同庞贝古城一起被维苏威火山摧毁的古罗马古城里,就有一幅壁画描绘着橘黄色的蘑菇,是艺术史上最古老的以菌类为题材的作品之一。
菌类那种微妙、浓郁、甚至可以与肉类媲美的风味,让无数人痴迷其中,即使在食菌的当下,内心依旧渴望着更多。
13世纪之前,中国便有以霉月断树,置深林中,密斫之,蒸成菌的尝试,到了南宋,中国人又开始用原木砍花法在圆木的表面种植蘑菇,成为世界上第一批人工培植的食用真菌。
到了17世纪,法国人发现真菌孢子并应用于农业,白色口蘑被成功培育。据说在拿破仑时代,巴黎附近的采石场坑道中,更是随处可见蘑菇养殖的踪迹。这些靠着饲肥、稻草和土壤生长的菌菇,几乎直到收获那天,都要待在黑暗的室内,养菇人要小心翼翼控制着湿度和温度,才能确保它们的收获。
这个世界上可以食用的菌类有上千种,但其中只有几十种被人们成功栽培出来。在广阔的森林里,还有另外一些菇蕈,更热爱自然和荒野。
这些共生型菌类仍需要在野地采集,它们生长在活乔木的身上抑或是周围,想要大量生产,首先要拥有一整片森林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诸如牛肝菌、鸡枞菌和松露等野生菌才会那么珍贵,凭借着比普通蘑菇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身价,站在了真菌价值链条的顶端。
为了追寻野生菌的踪迹,无数人纷纷踏上了旅程,采菌这条路,一走就是几百年,可见这散落在林间山野的菌子,对人们的味蕾是何等吸引。
无论是法国的的佩里戈、意大利的阿尔巴,还是中国的云南,都有这样一群采菌人。以采集各种野生菌为生的采菌人和松露猎人们,心里都有一份历经了无数次的地图,掌握着菌子们的秘密。
据说松露猎人为了不让人窥探到他们获取松露的秘密,只在夜间出没,手持照明灯,随身携带挖掘松露的小工具,身边还带着经过训练的松露猎犬,只为找到深埋于地下的小小菌块,那些轻薄的松露,连带着其中密密的回纹,四两拨千斤,好像确有一种魔力。
同样,在汪曾祺的笔下,云南的初夏是云海涌动下的潮湿,以及森林里悄然生长的野生菌。五月份的初雨,就能唤醒第一批菌子。多雨的季节,云南的山林是菌子最大的舞台。野生菌们会按顺序纷至沓来,而唯有有经验的采菌人才能将好菌悉数全收。这不单单靠眼睛,还要靠鼻子,靠感觉,以及依靠对林地的熟稔。
一颗颗野生菌,在语境中已经超脱了其含义本身,成为人们苦苦寻求的口腹归宿。
老一辈的云南人,喜欢在菌子收获的季节,反复讲给孩子们讲述小时候把采到的松露喂猪的趣闻。菌子在他们的心里不分高低贵贱,只有好吃不好吃的区别。而保守的英国人干脆对所有菌类都抱有怀疑态度,除了普通蘑菇,他们很少会把野生菌带进厨房。菌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摇身一变,从来自土地的意外惊喜成为贵族餐桌上的点睛之笔的呢?
从15世纪开始,随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风潮以及大航海时代宗教禁锢的松动,大量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松露的描写。松露独特的味道,令人联想起欲望与荷尔蒙。再加上大航海时代之后人们对于香料的追捧,使得带着奇异香气的松露广受贵族的喜爱,简单如酵母、大蒜、奶酪、蜂蜜,复杂如麝香、泥土、藿香、青草,一块小小的真菌,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风味标签。
如此,黑松露开始出现在贵族烹饪之中,例如在野禽、生蚝乃至以鹅肝酱为代表的法式肉酱(pâté)中,都能寻觅到松露的踪影。
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、法国现代烹饪之父——玛丽昂端-卡汉姆(Marie-Antoine Carême)。卡汉姆系统整理了法国烹饪技法与料理门类,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法餐的雏形,在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刀的一场晚宴中,他设计了一道名为Salmon à la Rothschild的料理,是将一条巨型三文鱼浸在四瓶香槟中,重达一磅的松露被切成半月形的薄片放置在鱼身上,伪装成鱼鳞的样子,奢华程度可见一斑。
无独有偶,白松露也遇到了自己的卡汉姆——意大利酒店巨头贾科莫·莫拉(GiacomoMorra)。1949年,贾科莫与政客名流合作,举办了一场年度最佳白松露的评选,其中便包括玛丽莲梦露和英国首相丘吉尔。
为了凸显松露的新鲜与血统,餐厅侍应生往往会用一种名为AffettaTartufi的特殊刨具,在客人面前把松露削得菲薄如纸,一片接着一片轻盈地落在盘中。这传统延续至今,松露雨也就此成为网红炫富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。
松露凭借一己之力,在西方建立起野生食用菌类的价值体系,并且登上了菌类世界的价格顶端。而数百年后,当法国传教士来到云南时,才发现这种昂贵的菌类已经在我国古老的土地上沉睡了数百万年,却顶着猪拱菌、土茯苓这样的诨名鲜为人知。
不仅有松露,日本人为之疯狂的松茸,在云南也能找到踪影,甚至品质更高。1949年之后,菌类的出口创汇让云南人找到了新的致富路径,菌类的价格也因此一路上扬。
近十年来,云南的野生菌开始逐渐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餐桌之上,从最初便于保存的腌干巴菌和油鸡枞,到今天依旧当季的脆嫩鲜菌,当地对菌子的人工促繁、野生采集、分类加工、包装运输也渐成气候。诸如干巴菌这类本是自产自销的野生菌,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增大,不少地区便以包山菌代替野外采摘,反而更容易分级与运输。
云南的野生菌背后,已然演化出一整套产业链条:冰鲜技术的发展,使得当天采摘的野生菌,次日就能为其他人享用,在新鲜程度和口感上,甚至可以到达八成以上的保留。在一线城市的生鲜超市,每当食菌季节到来,人们哪怕不踏进滇地,也能坐享其成。
雨季一到,诸菌皆出,空气里一片菌子的气息。 到今天,云南已知的野生食用菌已达800多种,约占国内的百分之八十之多,接近全世界食用品种的一半。从滇北迪庆到滇中楚雄再到滇南普洱,云南地区遍布的山野与林地,就像是一个永远也探索不完的菌子王国。和近几年大火的松露松茸相比,云南人更青睐鸡枞的清甜细腻,牛肝菌的肥嫩浓郁,以及干巴菌的柔韧松香。除此之外,常见的菌子还包括青头菌、老人头、鸡油菌、羊肚菌等。
作家阿城在《思乡与蛋白酶》里写道说到鲜,食遍全世界,我觉得还是云南的鸡枞菌。用这种菌做汤,其实很危险,因为你会贪喝,喝到胀死。除了煲汤,鸡枞的吃法也变换万千。一把青花椒、几片云腿,清蒸出的鸡枞再不需要多余的调味,便能点化出无边的鲜美。当季的鸡枞菌吃不完,撕成丝进油锅,便成了油鸡枞,浸在油中密封于罐,吃粉面时舀上一勺轻轻一拌,鸡枞的鲜香脆嫩又徐徐展开,成为不容争辩的味道。
如烹饪不当,会让人误食毒素,产生幻觉见小人、见精灵的见手青,具有伤变后的显色反应特征,手起刀落后呈现出靛蓝的青色,也为菌子传说增添了不少奇幻的色彩。
连同见手青在内的牛肝菌,切得厚薄一致,猛火蒜片爆炒出香,镬气与菌子的鲜融为一体,辅料只要油和盐,偶尔中间还会混有一两朵青头菌,滋味更是特别。如此一来,炒出的菌子口感细腻、香气浓郁,据说连当年西南联大的食堂里都有这么一碗。
干巴菌形如海底的黑色珊瑚,菌帽小而紧促,清理步骤繁琐,分寸拿捏不好就会破坏口感,属于中吃不中看的野生菌。干巴菌的香味十分浓烈,炒起来整条街都闻得到,一盘街边小馆的干巴菌炒饭,就足以把色香味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干巴菌,菌也,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,宁波曹白鱼鲞香味,苏州风鸡香味,南京鸭胗肝香味,且杂有松毛的清香气味。 在昆明居住过6年之久的汪曾祺,谈起干巴菌,更是恨不得把南北菜系之香全都用上。
因为颜色鲜艳,如同鸡油,即使是采菌新手也不会错过。鸡油菌烹饪方法灵活多样,尤其适合炖煮鸡汤,有种淡淡的杏仁香气。
野生菌散落在山林间,本不属于云南人的主流饮食体系之中,正如云南美食作家敢于胡乱所说的那样:不少云南人,仅仅把野生菌看作一种寻常时令菜,并不认为那是多了不起的山珍。无论之前鲜有人问津的松露,还是被当地人笑称为山寨鸡枞的松茸,在被菌山包围的云南人心中,似乎都不值得一提。
当地最贵的野生菌
虽说人们常常用松茸的价格作为云南野生菌的噱头,但其实真正的王者属于干巴菌,年年都是昆明水木花野生菌市场的价格冠军。在云南人民心目中,松茸、松露、鸡枞、虎掌菌与之相比,只嫌俗气与平庸。
何时买菌最划算
刚上市的菌子产量少,价格昂贵,等到旺季来临,售价通常会缩水2-5倍。像松茸这样的豪华型代表,甚至价格会缩水10倍以上。要耐心等待云南雨季的来临,每当雨后,野生菌就会破土而出,菌子的价格也会随之回落。
最好的烹饪方法
面对一小篮新鲜的野生菌,怎样对待它才算不辜负肠胃?最正宗的云南做法是加一点腊肉,用青红辣椒烹炒,或者买一只肥嫩的母鸡熬成鲜菌鸡汤。越来越多的餐厅不拘泥于传统,将野生菌切片炭烤,或将安全的可食用菌做成刺身,也成为常规吃法。但在炒制前,野生菌需要先在沸水中煮3-5分钟,漂洗后再加工,以免食物中毒。
野生菌的一生,每一天都在成长,直至被发现,然后它的生命开始被接受、欣赏和赞美。一只菌子的背后,是天、地、人凝结起的风土,囊括了一切对土地、气候、人文传统的无比热爱与尊崇。
编辑:若菲
文:林爱肉
视觉:卞玉清
摄影:陈辉州
部分图片:视觉中国
插画:王沫沫
场地协助:一坐一忘云南菜(三里屯店)
文章来源:《时尚COSMO》6月刊
图片来源
时尚COSMO / 视觉中国
新媒体设计
甲丙Wayne
﹀
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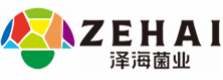
 鲁ICP备18004870号-1
鲁ICP备18004870号-1 微信联系
微信联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