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小丁
杨疯子一辈子生了十多个孩子。
这么多年来,杨疯子在村里人的眼里,总是很复杂,充斥着同情和谴责。这样的悲剧对于上一个时代的人,特别是山区的人来说,司空见惯。
当我把她的故事讲给友人听时候,很少有人能接受,不是不相信这样一个故事,而是极少有人明白她一个怎样的人,活的是一个怎样的状态。
杨疯子是我的二伯母,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,从我记事的时候,我就知道大家都叫她杨疯子,我不这么叫,我叫她伯母。伯母比我父亲大几岁,个子高身体壮,长得也很漂亮,是村子里贤惠的媳妇,干活是一把好手,又会过日子,家里粮食从来都不缺。刚嫁到村子里的时候,人人都夸伯父找了个好媳妇。
父亲说他和母亲刚分家的时候,自己种庄稼的水平不行,都是伯母和伯父给帮忙种粮食,有时候缺粮的时候,伯母也会给母亲送来一些。
伯母是个命苦的人,所有的好日子都从伯母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结束了,伯母一生都在为生一个儿子苦苦挣扎,挣扎到用尽了全部的生命。
伯母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,也就是我的志娟姐姐,姐姐比我大几岁,早我几年上学,我两岁的时候她上小学一年级,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她还是上小学二年级,我小学毕业的时候,她退学了。
志娟姐姐长的很好看,但是反应比较迟钝,非常喜欢笑,我很喜欢志娟姐姐带着我玩,她经常会从家里偷一些油和盐,带着我在河里摸鱼,然后在沙滩上生火,用盘子煎鱼吃。有时候也会偷别人的花生,装在水壶里煮着吃,煮的花生里撒上一把从家里偷的盐,非常美味。
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志娟姐一起度过的,那条小河那片沙滩是所有村里孩子的乐园,但是现在早已被挖的千疮百孔,就如同记忆和生活一样,面目全非。
村里人都说志娟这女子脑子笨,就不是上学的料,长的还算灵性,过几年就近找个婆家过日子。
九十年代中期,打工的浪潮开始兴起,志娟提出要出去打工,村里人说,这女子的脑瓜子,出去都找不到回来。跟大家想的一样,志娟姐出去后,就没有回来。若干年以后,才听人说她被人卖到河南的一个山沟沟里,再一次回来的时候,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。
我对志娟姐的记忆很模糊,甚至忘记了她的样子,我只记得她见人就笑,在家很勤快,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时候,她对我很好,其他记忆几乎一片空白。
伯母生的第二个孩子还是个女儿,是我的二姐姐志新,生完二姐后,伯母慌了。二奶奶骂这个儿媳妇没用处,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,伯父也板着个脸,对伯母拳打脚踢,二姐生下来后,就不怎么招人喜欢,又因为是第二胎,计划生育不让再生了,伯父更加暴躁,有事没事就会打的伯母满村子跑。
生了二女儿志新后,伯母经常受到责骂,但依然很勤快,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,地里活她一个人全包了,伯父出去给别人卖工挣点零花钱。
农闲的时候,伯母会找母亲一起上山去挖药材卖钱,伯母给母亲说,生娃一定要生个男娃,不然在家里没地位,在咱这农村里,儿子多才会势力强,做啥事屋里屋外都没人敢欺负,以后儿子还可以给咱养老送终,生一个还不行,得生好几个,这样腰杆子才能挺得直。
后来母亲生了我和弟弟两个男娃,伯母对我们非常好,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,母亲说,伯母是个好女人,一定会生个儿子。
小时候计划生育很严,到处都张贴着宣传口号,宁多十个坟头,不多一个人头,全乡上下,乡干部带领干部队伍到处抓超生的人,一时间腥风血雨,打胎,结扎,罚款,拉家具,蹲派出所,甚至直接把人打死,整个村庄人人自危,一片狼藉。
伯母在这个时候怀上了第三胎,全家人都甚为紧张,生怕透漏出去半点风声。伯母整天在家里不敢出门,生娃的前一天晚上,才偷偷的把我奶奶叫去给接生。这一次欢天喜地,生了一个儿子。伯母很高兴,但不敢声张,在家里抱着儿子笑,还给孩子起了个贵气的名字成宝。
成宝的到来给这个家庭添加了一丝欢笑,但这短暂的欢笑很快就没有了。农村里的卫生条件比较差,生成宝的时候,奶奶接生时用剪刀剪断了系带,出生没几天肚脐就开始感染,慢慢出现溃烂,最后还生了蛆,成宝没有熬太久,满月的那一天,夭折了。
三天后,村里人都知道,伯母疯了。从此杨疯子成了伯母的唯一称呼,甚至到最后,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。
伯母成了疯子以后,村里人都离的远远的,我经常看到伯母抱着一个枕头,用红布包着坐着门口,给孩子喂奶。不过伯母的疯时好时坏,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,疯的时候就到处乱跑,打人骂人。
有一年过年,伯母来到我家,非要硬塞给我两块钱压岁钱,让我有时间去她家坐坐,陪她过个年。我非常害怕,不敢接伯母的钱,志娟姐姐跟我说伯母做了好多好吃的,就等着我去了。最后我跟着母亲一起去了伯母家过年,母亲说,既然伯母这么喜欢我,就让我给伯母做干儿子吧,伯父和伯母非常开心,连续好几个年都让我去他家过年,伯母说干儿子也是儿子,有儿子比什么都好!那几年我经常去伯母家吃饭,伯母也很少疯了。
伯母家门前种了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橘子树,每到苹果长出来的时候,伯母会经常坐在院子边看着,防止小孩子来偷果子。果子成熟了,伯母会给我送来一些,这是我小时候吃的为数不多的水果,记忆特别深刻。
伯母也比以前爽朗了很多,日子过的顺顺当当,偶尔犯病跑了,也会很快回来。我也不那么害怕伯母了,放学会和志娟姐一起坐在苹果树下写作业,天天期盼着苹果早点成熟,就如同伯母天天盼着生个儿子一样。
上小学的时候,山村里开始流行一种门头教,是基督教的一种,传说信这种教可以心想事成,多福多贵,伯母一心想要个儿子,就跟人信了村里的门头教。
伯母经常给我说,让我跟她信教,世界末日马上就来了,除了他们之外,所有的人都会死,以后也不用干活,天上会给他们下粮食和钱。我似懂非懂,以为伯母又发疯了,她说的话不可信。后来伯父也跟着伯母信门头教,到处传教聚会,伯母还当上了小头目,每月可以领到几十块的工资。这些都是我听人说的,我没有亲眼见过。我每天看到伯母晚上从外面回来,我就知道她又出去宣传世界末日了。现在想起来,这样的传教只有在特别落后的地方才会传播,当所有人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时候,才祈求信仰可以带来福贵,渴望世界末日的到来,愚昧让太多的人失去了理性,失去了原本积极劳动的本分。
伯母当上小领导后,伯父跟着伯母信起了门头教,这个时候伯母又一次怀了孩子,而且是个双胞胎。为了防止计划生育的人突袭,伯母把安胎的地点选在了深山里的娘家,数月不敢回家,村里人都说伯母外出打工了,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但临生前不久,还是被乡上的干部找到了,伯母偷偷的躲在山上不敢回家,等乡上的干部都走了的时候,伯母已经在山上自己生出来了这对双胞胎,而且是个龙凤胎,伯母把男婴抱在怀里,怕男婴受到一点冻,但面对女婴的时候,伯母迟疑了,她怕把这个女婴捡回去后,遭到婆婆和伯父的谩骂,处于母爱的本能,她最后还是把两个孩子都抱回了家。
因为超生,伯母家被处于重罚,家里值钱的家具和粮食都被计划生育的干部拉走了,伯父和伯母依然欢喜,有了儿子就给整个家庭长脸了。
那个年代很少有奶粉给孩子吃,主要靠母乳喂养,伯母缺乏营养,奶水很少,她把所有的奶水都喂给了儿子,女儿只给喂一点水和面糊糊,几个月以后,女儿因为饥饿和生病,夭折了。伯母就像解脱了一样,抱着自己的儿子出来在村子里转悠,也不害怕计划生育的人突然上门把她抓走,她眼里只有儿子,有了儿子她就有了所有。
人都说,双胞胎是不能分开的,小时候如果分开了就很难存活,伯母不听人劝,依然选择丢弃了女儿。正如人们说的一样,一个月后,儿子也跟着女儿一同夭折。
从这以后,杨疯子更疯了。
后来,伯母陆续又生了几个孩子都是女婴,生下来就直接被扔进了河里。我们在河里游泳的时候,还遇到过扔掉的女婴,村里人都说这女婴是伯母扔掉的。
伯母疯了以后,就不再出去跑门头教了,一发病就到处乱跑,有时候一连几个月不回家,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到处寻找,后来慢慢的村里人已经习惯了杨疯子的失踪,她总会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自己回家,也很少有人关心她去了哪里。
伯父自从信了门头教后就不和村里的任何人来往,整天外出宣传门头教。在一次传教回来的路上,伯父骑自行车掉进了河沟,村里人找到伯父的时候,伯父伤的挺重,小腿骨折,头也磕破了。当村里人把伯父送到医院的时候,伯父却偷偷一个人跑回家来了,伯父说神灵会保佑他痊愈的。随后的几天,伯父叫来好多的门头教徒一起给他祈祷治病。三天后,伯父血流干了,倒在了自己的炕头。
伯父下葬的时候,给志娟姐打电话,志娟姐的婆家说忙,不让志娟姐回来,村里人凑钱把伯父给葬了。
伯父离世以后,伯母头发全白,彻底的疯了,经常遇见人就打,刚结婚不久的志玲,把伯母锁在房子里,不让她出来,每个月给送一次干粮,主要送冷馍和自来水。
为了防止伯母在家把房子点着了,房子里所有的火源都被收掉了,包括电源。伯母吃喝拉撒都在这个房子里,我路过伯母房子的时候,经常看到门缝里一只闪亮的眼睛看着外面,然后是撕心裂肺的抓喊,我撒腿就跑,害怕伯母会破门而出,把我撕个粉碎。
有时候母亲会从门缝里给伯母递一碗热饭,我问母亲,为什么不让伯母出来活动,母亲说,现在已经没人管她了,志新这个唯一在身边的女儿也不再理会这个疯子妈,这样的人命苦着呢。
志娟姐自从嫁出去后就回来过一次,志新除了每个月给伯母送一次干粮外,其他时间从来不回村子。我经常听到房子里发出来的哀嚎,在这样的环境下,即使是正常人,也会给憋疯的。
杨疯子渐渐的哀嚎声音少了,有时候甚至悄无声息。村里人以为杨疯子死了,当志新打开门看的时候,伯母像极了电视里的白发魔女,满脸皱纹,一头白发,一声嚎叫,从志新的身边破门而出,消失在村子的尽头。
对于杨疯子的失踪,大家早已习以为常,但这一次,杨疯子却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,村里人也派人到处打听过,都没有找到杨疯子。
志新依然忙着过自己的日子,好像自己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妈一样。后来有人说,在邻县见过杨疯子,也有人说,有人在县城边的垃圾场看到过她的尸体,但再也没有人见过杨疯子回村子。
过年回家,路过杨疯子的老屋的时候,院子里长满了草,门前的苹果树已经渐渐枯萎,衰老的枝桠上冒出一两个苹果花蕾,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涌上心头。
偶尔和母亲聊起来杨疯子,母亲感叹说,人没了就没了,省的再受这世间的苦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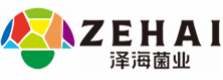
 鲁ICP备18004870号-1
鲁ICP备18004870号-1 微信联系
微信联系
